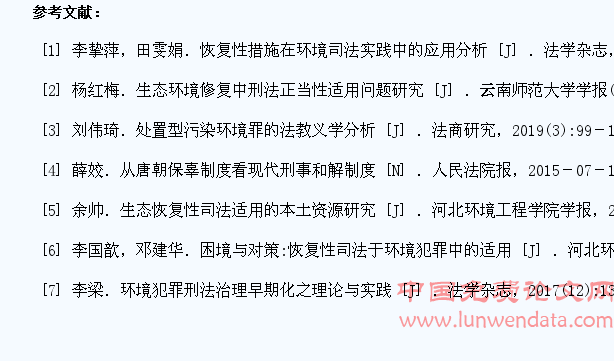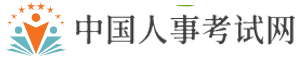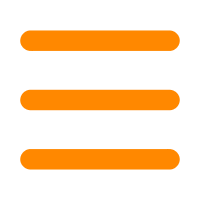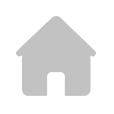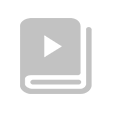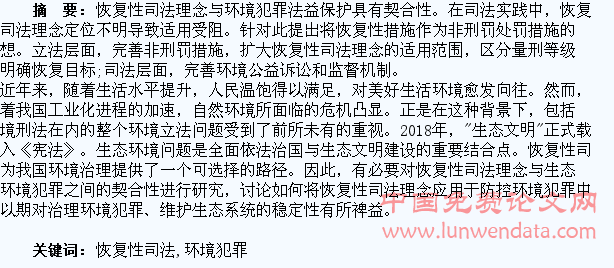
1、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观的契合与进步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观的契合
在国内法治进程中,环境犯罪所保护的法益颇具争议。大家以《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最典型的污染环境罪为起点对环境法益做出理解。2011年《刑法修正案》把原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订为“污染环境罪”。在罪状描述中以“紧急污染环境”的行为标准替代原罪名中“致使重大环境事故,导致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导致人身伤亡的紧急后果”的结果标准作为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新罪名扩大了环境犯罪打击的范围。同时,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观也发生了变化,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架构由结果犯逐步向危险犯转变,其所秉持的法益观也由人类中心主义逐步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2020年《刑法修正案》第三对污染环境罪的条文进行修订,此次修订提高了法定刑的量刑幅度,更为详尽地规定了四种法定刑的升格条件,其中前三款规定只须犯罪行为对环境导致紧急污染、永久性破坏的,就能认定为合乎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在一定量上承认了生态环境资源是环境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强调了生态学法益保护的要紧价值。
在生态文明年代建设背景下,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需要是对被破坏的环境应当进行修复;恢复性司法理念作为刑事司法范围新兴的犯罪控制理念,该理念的核心是对受损法益既要重视恢复的过程,又要重视恢复的结果,其核心价值与国内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具备高度的契合性。环境犯罪侵害的对象是环境,环境治理的核心是对被破坏的环境进行修复。恢复性司法理念适用在环境犯罪治理中既有益于达成修复被犯罪行为损害的环境法益,又有益于修复被犯罪行为损害的生态环境,使得生态系统平稳运行。因此,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具备契合性。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观的流变
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国内立法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其雏形为保辜规范。保辜规范滥觞于西周时期,在唐代臻于成熟,在国内传承了数千年之久,具备顽强的规范生命力。保辜规范是指犯罪人基于真诚悔罪,主动向官府提出,自觉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以达到消除彼此矛盾、平复社会关系的目的,最后由官府视弥补状况决定对其是不是从轻,与从轻幅度的规范,可以说其是保护被害人的法律规范。保辜规范看重修复犯罪人所损害的社会关系,并依据修复程度决定刑罚轻重,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价值追求。此外,汉代的无讼规范和春秋时期的“亲亲得相首匿”规范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价值追求。
近代以来,伴随工业迅猛进步,环境态势急剧恶化,以惩罚和预防为主的传统刑法理念不能满足对环境法益保护的需要,国内开始探索在环境范围引进恢复性司法理念。立法上,2010年修订的《水土维持法》第49条规定:违反规定开垦开发农作物土地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退耕、恢复植被等弥补手段。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5条中确立了“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环境治理原则。2020年拟定和公布的《长江保护法》特设“环境修复”一章。司法上,国内的刑事和解规范、附条件不起诉规范、社区矫正规范都在一定量上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价值追求。学术界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探索与司法实践的不断进步,其实质都是对恢复性司法规范核心理念的践行,并致力于为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展开和进步谋求新的理论与思想进路。
2、恢复性司法理念适用于环境犯罪中的应然定位
作为酌定量刑情节
恢复性司法理念应用于环境种类犯罪,主要表现为对受损害生态环境的修复,量刑上是酌定量刑情节,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对破坏环境类的犯罪在量刑上参考犯罪人对被破坏环境的修复程度。犯罪人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分为两种状况:第一,是犯罪人将受损害的生态环境予以主动修复的行为,可以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程度,与其再犯的可能性等;第二,将犯罪人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或者使用切实有效的方法阻止污染继续发生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有益于鼓励犯罪分子排除污染,降低对环境导致的损害,是准时止损、保护生态环境的要紧举措。将恢复生态环境作为量刑情节侧重于在量刑过程中恢复被害人因环境污染行为所遭受的损害,是犯罪者主动发起推行的,可以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减少,意在鼓励行为人主动修复生态环境,维护生态进步。
恢复性手段在审判实践中被当作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虽然起到了肯定的社会成效,但囿于立法的经验、技术尚不成熟,法律对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粗化,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因规定的模糊性导致法官对酌定量刑情节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适用并不规范,相似案件却得出了迥异的结果。由此看来,尽管实践中恢复性手段作为酌定量刑情节适用广泛、立竿见影,但站在生态全局观视线来看,其所致使的裁判随便性和不确定性不容忽略,很难反映出恢复性司法的弥补手段和量刑之间的联系,很难真的提升司法效率、达成个案量刑正义。虽然国内在2016年颁布了有关的司法讲解,但其适用条件严格,仅仅适用于轻微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且仅适用于初犯,这使得大多数犯罪者对这种酌定量刑情节关注度低,认识不够,惰于推行环境修复行为。
恢复性手段作为非刑罚处罚手段的正当性
当下,环境种类犯罪的刑事制裁方法使用自由刑与罚金刑方法。由上文可知,这具备非常大局限性,不利于对环境污染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后果起到修复用途。现在国内刑法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依据主如果《刑法》第37条的5种非刑罚处罚手段,但就现在的司法近况来看,其非常难达成惩罚犯罪和恢复受损法益的双重成效。恢复性手段作为非刑罚处罚手段应用于环境犯罪中有其正当性。
从理论层面看,恢复性司法手段作为非刑罚处罚手段有其正当性基础。第一,恢复性手段具备广泛的适用对象。非刑罚处罚手段主要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风险不大的刑事案件,环境犯罪行为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犯罪动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程度低。第二,非刑罚处罚手段的非刑罚性,是“恢复”二字的题中应有之义。非刑罚处罚手段对于有的免于刑罚处罚的犯罪分子而言,既达到了警示、教育的目的,又使其免受“前科标签”的困扰,有益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也勉励其积极主动履行环境修复责任。最后,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非刑罚处罚手段的目的除去惩罚、教育以外,更要紧的是对法益的恢复。恢复性手段要以环境修复为目的,依据个案小心选择。恢复性手段兼具对犯罪人惩罚和环境法益补偿的双重功能,其作为非刑罚处罚手段,一方面可以震慑犯罪人,起到惩罚和避免的双重成效;其次也有益于法益恢复目的的达成。
从实践层面看,恢复性手段适用于环境犯罪中获得了好的社会成效。目前,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是在传统正当性理论影响下形成的,并未体现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未引入修复生态环境的刑事责任承担方法。为突破环境犯罪立法滞后性的难点,全国多地法院对审理环境犯罪案件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践行进行尝试,法官为审理案件的现实需要在判决书中革新出增殖放流、劳务代偿、补植复绿等生态修复方法。如2017年四川荥经县程某在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状况下,对自己承包的林地进行清林、造林,滥伐林木、盗伐林木。四川荥经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构成滥伐林木罪、盗伐林木罪,数罪并罚判处相应刑期,并责令被告人程某补种指定树种241株。在上述实践案例之中,法院判决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补种林木,自己破坏的自己补植复绿,收到了好的社会成效。因此,在将来修法时应当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手段,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补足立法阙如。确立非刑罚处罚手段在法律中的明确地位,以便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有法可依,司法机关就能在判决文书中明确环境恢复主体,明确恢复责任和恢复目的等,从而既达成了刑罚的惩罚目的和预防目的,又与生态学人类中心法益观相统一,增强了生态修复的可操作性。
3、恢复性司法适用于环境犯罪的具体展开
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的适用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立法层面,应当补足法律规范的缺失,健全非刑罚手段和环境犯罪的刑法体系;二是司法层面,从健全环境犯罪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融合,到健全恢复性司法手段的监督体系的构建。
法律规范的补足与融合
1.健全非刑罚处罚手段
在司法实践中,非刑罚处罚手段在环境犯罪治理中适用率高,且起到了好的社会成效,但因立法未明,司法先行,致使其虽可以在一定量上起到威慑用途,但有“没办法可依”之嫌疑。在当下法治社会背景下会让犯罪人觉得没法律依据,很难促进犯罪人自觉对犯罪行为所致使的污染后果予以弥补,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破坏环境修复的法律依据问题。惩治环境犯罪应当预防与惩罚并重,非刑罚处罚手段与刑罚一同达成着刑事制裁的目的,对保护法益有着要紧意义。本文觉得应当在《刑法》第37条中进一步明确生态修复手段及其适用对象和范围,如此防止了“没办法可依”,成为有法可依。在修订《刑法》第37条时,把生态修复责任的承担方法明确写入刑法条文之中;把散见于部门法与环境治理有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讲解进行整理,写入非刑罚处罚手段之中,使法律明确化,体现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在刑法中明确生态恢复的非刑罚处罚手段,既能够让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准时得以恢复,又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法律依据,让司法机关有法可依,让司法裁判愈加权威,更能达成司法在治理环境犯罪的法律成效与社会认可成效的统一。
2.构建愈加健全的环境犯罪体系
恢复性司法理念适用于环境犯罪中应当进一步细化适用规则,结合司法实践,健全立法,构建愈加科学的环境犯罪体系。第一,扩大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国内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规范、附条件不起诉规范、社区矫正规范都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学术界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探索与司法实践的不断进步,其实质都是对恢复性司法规范核心理念的践行,这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进一步展开与进步提供了思想进路和理论经验。然而,现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当地化实践体现为一些碎片化的理论内容,没完整的规范支撑。国内刑法对污染环境种类犯罪规定了自由刑和罚金刑的处罚方法,但并未明确将恢复性司法规定为刑罚手段或者非刑罚手段,这就致使在审判实践中,恢复性司法手段多应用于森林污染、土壤污染的修复之中,范围狭窄,应用甚少。污染环境罪侵犯的客体具备复杂性、多样性,不只包括大方污染、土壤污染,还包括水污染、矿产污染等多个层面。立法的滞后性致使恢复性司法理念很难广泛应用于污染环境种类的犯罪中,鉴于此,大家呼吁进一步扩大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适用范围。第二,区别量刑等级,明确恢复目的。《刑法修正案》针对四种紧急污染环境行为提高了法定刑档次,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了污染环境犯罪量刑精细化的立法趋向。刑罚公正性的一个要紧指标就是量刑的一致性。世界上没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也没一模一样的两个案件,因此为了尽可能做到量刑的一致性,做到法律面前每人平等,大家应当依据污染状况,区别量刑等级,明确其应当承担的恢复目的。本文觉得,应当进一步打造统一完备的专家评审机制,对导致不同程度污染的犯罪行为,综合其主观恶性大小,进一步细化法定刑幅度。除此之外,因为污染环境种类犯罪具备多样性、复杂性、流动性等特征,不可以对其设立统一的恢复目的,应当依据污染程度和可逆性的程度,综合判断其可能达到的修复目的,并可视其恢复状况,由实行机关决定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进一步明确修复目的。
实践层面实行机制的考虑
恢复性司法理念应用于司法实践层面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1.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融合污染环境的行为具备广泛风险性,其刑罚假如仅仅聚焦在惩罚犯罪上,不关注对受犯罪行为所损害环境的修复,没将所获得的罚金专项用于修复生态环境,那样社会公众的环境法益就很难得到救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179件,审结58件,同比增长175.4%和262.5%。受理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2309件,审结1895件,同比增长32.9%和51.4%。2020年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557件,同比增长82.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国内环境公益诉讼的数目逐年提升,特别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数目持续攀升。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针对环境行为的救济方法,具备应用的广泛性、普惠性等优点。大家应当积极探索怎么样进一步健全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框架,尤其是丰富公益诉讼规则,使其体现恢复性司法理念,体现生态环境的可修复性。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环境公益诉讼从两个方面进行融合:第一,在司法层面上打造行刑责任可依法转换的衔接机制。公益诉讼行刑责任交叉案件的裁判可以结合行为人推行恢复性手段的状况作为分配基准,必要时司法机关可以视公共利益的恢复情况决定违法行为人的责任转化。如行政机关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后,行政相对人怠于缴纳,此时检察机关因环境遭到紧急破坏提起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有的行为人会立刻按需要缴纳罚款,法院可在依据《刑法》第37条第2款判决赔偿损失时,对有关状况予以考量。赔偿损失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分子,恢复受损法益。假如行为人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有可恢复性,其在案件审结前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恢复因其犯罪行为受损的生态环境,本文觉得,司法机关可以在专家指导下,结合环境恢复状况,考量将赔偿损失的刑事责任转化为行政责任,减轻司法机关的诉讼重压。两种责任承担依据虽然在功能上有所差异,但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救济与恢复是共通的。第二,将代履行方法融入环境公益诉讼中。代履行方法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讲解中,并未直接规定于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公益诉讼裁判应当兼顾环境法益的恢复和司法效率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使得环境污染者非常难独立完成修复工作。本文觉得,司法机关可以在公益诉讼实行过程中,依据案件状况选择适用代履行方法,针对不具备人身依靠性、被告人没能力亲自完成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委托具备专业能力的第三方实行修复策略,由被告人承担相应成本。将代履行方法融入环境公益诉讼中是恢复性司法理念深入贯彻的结果,既可以使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准时得以恢复,又提升了司法效率。
2.健全恢复性手段的监督体系
健全恢复性手段的监督体系,应当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实行部门有效联动。实行部门有效进行协同监督可以形成监督合力,也分担监督本钱,节省司法资源。环境污染具备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修复生态环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为加大实行监督力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应当针对每个部门的工作和职责,构建精确化的实行监督分级系统。
合理配置各实行部门的实行监督权力,进一步明确实行主体的监督责任,畅通实行部门的交流途径,不能随便滞涩实行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减少实行效率。可以考量依托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提升采集信息的能力,构建横跨实行部门的司法链条,充分借助网络视频会议等交流途径,使用多样化的交流方法,创建更高效的实行衔接体系,自行为人开始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起将跟踪信息录入链条,使恢复过程留痕,加大各部门联动实效。其次,打造有效的实行成效评价体系,以责任监督的方法督促实行部门担责。伴随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进步,环境修复考核评价系统有哪些用途愈发凸显。大家应当加大对传统环境考核指标的审视选择,改进环境恢复考核方法,构建自动化信息化的监管考核模式,“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考核方法,促进实行部门主动进行生态恢复成效的监督工作。第二,健全政府主导、社区监督等监督机制。国内恢复性司法判决实行过程中,由于现在的实行部门联动监督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有的实行监督部门履行责任消极、被动,致使法院判决大多缺少明确的验收主体和验收标准,导致生态恢复的成效监督失灵,使得恢复性司法的功用很难得到充分有效发挥。污染环境犯罪最大的受害者是人民,人民是污染环境犯罪损害的最后承担者,因此大家应当认识到治理环境犯罪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于群众,要充分合理的利用群众的社会监督力量。在司法实践中,大家应当使用多样化恢复治理模式,健全政府主导、社区监督的方法。具体而言,第一,健全政府主导的方法,借助政府资源,站在全局角度拟定有关政策,做好生态保护宣传工作。在传统报应刑理念的桎梏下,重刑轻民观念根深蒂固。
社会形态的变迁致使司法理念的变化,伴随环境法益独立价值的凸显,侧重惩罚与预防为目的的传统刑罚体系已不可以适应新年代背景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兴起与进步正是对传统刑法理论在生态全局观背景下弱点的补足。应当通过各种宣传方法使大家充分意识到要守好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才能流金淌银。第二,健全社区监督机制。恢复性手段的适用总是与缓刑相联系。群众是生态恢复成效的感受者。在恢复性手段的履行过程中可以大胆引入公众参与,借助社区监督的模式:一方面,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拓宽监督主体的范围,节省司法资源;其次,使得违法行为人推行环境修复行为时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感,有益于其重新回归社会。
结语
刑法作为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应当对怎么样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有力回话。然而,自环境种类犯罪在《刑法修正案》中确立以来,其刑罚方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刑罚适用成效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差距较大。在此背景之下,恢复性司法理念进入大家的视线,其有益于从根本意义上解决环境种类犯罪的遗留问题,为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云筑网。